



封面故事⑤
对生命的敬畏
让离别成为了人生旅途中
最特殊也最重要的一段
在生命的最后阶段
有这样一群特殊社工
他们把微笑带给每一位临终患者
陪他们从容安详地
走完生命的“最后一公里”
他们就是临终关怀社工
今天,殡葬一条龙4008341834故事的主人公
正是长期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社工
——谢佳洁
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

“小谢,你是个好姑娘,我们大家也都很喜欢你。但我还是不敢和你联系,因为一看到你就会想起我老伴。”60多岁的曾姨去世后,她的丈夫黄伯给谢佳洁发来了这样一条短信。
看着短信,谢佳洁鼻子一酸,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曾姨生前住院时的点点滴滴。她完全能够理解黄伯的那种感受,就像她自己也不太记得曾姨去世那天时的种种细节,比如,那天的天气怎么样、病床前都有谁在……
不仅是曾姨,似乎每一位临终关怀的病人去世时的情形,谢佳洁都记不太清了——仿佛潜意识里有一张硕大无朋的滤网,把这些记忆统统过滤了一遍。
“人呐,不管经历了多少事,殡葬服务多多少少还是会害怕生离死别。”谢佳洁说。

01
千里寻子半年
她带回了一盒骨灰

2010年7月,深圳的街头很热。肃穆的深圳殡仪馆前,50多岁的刘霞哭得双目赤红,滚落的泪珠碾过那张布满皱纹的脸,留下一道道清晰可见的泪痕。
“姨,耀斌出来了。”谢佳洁小心地捧着一个木盒子,从殡仪馆里缓缓走出来,一直走到刘霞身边。
木盒子里放着的,是刘霞的儿子耀斌的骨灰——他死的时候,只有28岁。
“儿啊!我的儿啊!”看着儿子的骨灰盒,刘霞瞬间瘫软在地。此刻,她那副瘦小的身躯,就像一艘在风浪里摇晃的小船,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。
耀斌不是刘霞唯一的儿子,殡仪馆却是她最牵肠挂肚的那个。17岁那年,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,给这个普通的广西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一击。用刘霞的话说,她不知道儿子那些年吃的药多还是饭多,“他的身体里好像住了两个人,时而清醒,时而癫狂。”
耀斌26岁时,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,独自一人来到广东打工。此后一年,他和家里还常有联系,但过了一年,便音讯全无。
除了刘霞,家里人对耀斌的失联保持着某种缄默——在农村,精神病患者就像是长在一个家庭身上的一道不愿被人提起的疮疤。但刘霞说,丧葬一条龙耀斌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,生病不是他的错,她一定要找到他,把他带回家。
于是,刘霞孤身来到广东,一边打零工一边找儿子。大半年后,她在深圳龙岗的一个桥洞里找到了耀斌。那时,他已流浪了很久,头发又脏又长,破旧的衣衫下,圆鼓鼓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。
不久后,耀斌住进了龙岗中心医院。长年流浪的他患有严重的肝腹水,多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
25岁的谢佳洁由此遇见了自己从业以来的第一个临终关怀病人。她说,耀斌清醒时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儿子,白事公司但不清醒时连母亲也不认得。
可惜的是,谢佳洁还没来得及问耀斌有什么话想对母亲说,他就溘然长逝了。他死的时候,刘霞心里的那片天好像突然塌了一样,眼泪一下子决了堤,哀嚎声响彻了整层楼。
哭干眼泪后,刘霞对医护人员说:“能不能请你们帮我儿子换身衣裳,我想他干干净净地走。”
谢佳洁说,这是刘霞说过的话里她印象最深的两句之一。还有一句是,有一天她在耀斌的病床前问刘霞有什么心愿时,刘霞看着病床上耀斌的脸说:“我要带他回家。”
谢佳洁和医护人员最终帮刘霞实现了心愿。他们为耀斌整理了遗容、换了一身干净衣裳,把他干干净净地送到了殡仪馆。那时,刘霞浑身上下连丧葬费也拿不出来,于是他们又为她捐了款,丧葬服务公司让耀斌得以顺利火化,和母亲一起踏上回家的路。
02
临终前
他给亲人写了一封长信

张伯是在2023年底成为谢佳洁的服务对象的。那时的他,癌症已到晚期,在医生的预测里,“最多还有一个多月的生命”。
第一次见到张伯时,谢佳洁显得有些拘谨。在临终关怀病房,死亡总是一个敏感话题。哪怕是谢佳洁这样入行十几年的社工,在面对一个仅剩几十天生命的老人时,说起话来也会格外小心。
“小谢,放轻松点。癌症嘛,不就放疗、化疗、做手术,没啥大不了的。我啥情况心里清楚着呢。”张伯看着她,笑着说。
这话让谢佳洁放轻松了不少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她发现张伯是一个非常乐观、开朗的人,殡葬礼仪服务总是喜欢给大家讲故事。
张伯讲故事的时候,他的妻子王姨就坐在病床前,和大家一起静静地听他讲。大家笑,她也笑;大家鼓掌,她也鼓掌。遇到老伴讲得不对时,她偶尔还会打断纠正。
王姨比张伯小几岁,她的身体也不太好,但还是每天守在张伯的病床前,给他喂饭、擦身子。有时,张伯睡着了,她会小声地跟大家吐槽自己的老伴:“他呀,就是个话唠,不让他说话就难受。”谢佳洁听了,心头一暖:这大概就是相濡以沫的样子吧。
转眼间,一个多月过去了,张伯的“大限”并没有到来。他开玩笑地对谢佳洁说:“看来老天爷想让我再多给你们讲几天故事。”
他把谢佳洁叫到身旁,说:“小谢,我想给我家里人写封信,我说你写好不好?”
“您想写什么呢?”谢佳洁很快拿来了纸和笔。
“我想简单回顾一下我这一生,对自己作个自我评价。再就是给家里人每人写一段话。”张伯说。
他的声音并不洪亮,却字正腔圆,将如烟往事娓娓道来。讲到老伴时,他瞟了一眼坐在一旁的王姨,有些害羞地说:“我很爱她,她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好太太。”他说完这话时,脸颊羞红了好大一块;一旁的王姨听了,也立马把脸别了过去,耳根子红了一截。
这封信最后写了一千多字。写完后,谢佳洁拿给张伯看。张伯逐字逐句看完,说:“不行,还得再修改一下。”谢佳洁便按照他说的改,一来一回,最后改了六遍。
谢佳洁说:“您可真是个认真的人。”
张伯哈哈大笑:“那可不,这可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篇作品,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”
张伯最终比医生预测的多活了一个多月。他走的时候脸上很平静,一旁的王姨也很平静,屋里的灯光打在他们脸上,像时间停止了一样。
03
“孩子,
妈妈好想看着你长大”

1981年出生的李念是两个男孩的母亲。她的离世,让谢佳洁至今都难以释怀,尤其是她临终前对三岁小儿子说的那句“孩子,妈妈好想看着你长大”,更是让谢佳洁每每想起便心痛不已。
2022年下半年,李念因为乳腺癌住进了医院。那时,她的大儿子刚上初中,小儿子将满两岁,生活的重担让她没法像其他病人那样一直待在医院安心治疗——她和丈夫都是来深务工者,工作不稳、收入有限,一旦生了病、没了活干,一家四口的生计便会失去着落。
医生们每次提到李念都会觉得可惜。他们说,如果她能规范治疗、坚持用药,结局很可能会不一样。
但李念的理由也很充分:如果她不去工作,一家人就交不起房租、吃不饱饭了。因此,每当病情稍有好转,她便会跑出医院去打零工。
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大半年。2023年2月,李念终究还是病入膏肓了,胸口出现了大面积溃烂,常常疼得整宿睡不着觉。她住进了临终关怀病房,遇见了小她几岁的社工谢佳洁。
谢佳洁把李念当姐姐看,说她是个乐观开朗的人,尤其擅长自嘲。比如,第一次见面时,她对谢佳洁说:“小谢,我们家住的可是毛坯房哦。”——她查出癌症的时候,江西老家的新房刚刚盖好,可还没来得及装修,钱就全花在医药费里了。
李念在病床上最享受的时光是和儿子们在一起。大儿子每周末会来医院看她,常常在她的病床前安慰她:“妈,我这次又考了前三名。你放心,我一定可以考上重点高中的。”小儿子在老家抚养,常常在视频连线时扮鬼脸逗乐她。
李念看着手机屏幕里的天真可爱的小儿子,有时会陷入恍惚。有一回,她跟儿子聊到中途,忽然放下手机对一旁的谢佳洁说:“我好想看着我的儿子们长大呀!”
还有一回,她不知看了什么新闻,自顾自呢喃道:“为什么有的人会不想活呢?活着多好呀,认真地生活、认真地爱人,多好呀……”
2023年3月,很想活下去的李念终究还是走了。在那之前,谢佳洁给她做了一本生命画册,里面全是她和丈夫、儿子们的照片。生命最后的时光里,李念常常抱着它翻来翻去,百看不厌。
十三年,四千多个日夜,数十位病人,在临终关怀病房,谢佳洁目睹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谢幕,也见证着一抹抹人间真情的涌动。或坦然,或不甘,或留恋,或释怀……每个生命的尽头,并非只有“死”的基调,也有“生”的色彩,哪怕只是窗外照进来的一抹光亮。
正是这些光亮,让我们不枉来这人间一趟。
(※除谢佳洁外,本文人物均为化名)

关于“封面故事”
飞速向前的时代,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,折射出一座城的万千气象、万种风情。那些深夜里汲汲耕耘的身影,那些晨光中静默无声的呐喊,那些逆境下奋力生长的群像,那些寄蕴于每一桩柴米油盐中的爱与责任,真实映照着一个个龙岗人的日常,共同构成了龙岗阔步向前的坚实轨迹。
关注深圳龙岗发布「封面故事」专栏,一起走近我们身边的龙岗人,倾听那些瑰玮动人的龙岗故事。
来源:龙岗融媒(首席记者 聂朦)
图源:受访者供图、视觉中国
责编:龙岗融媒(首席编辑 徐海燕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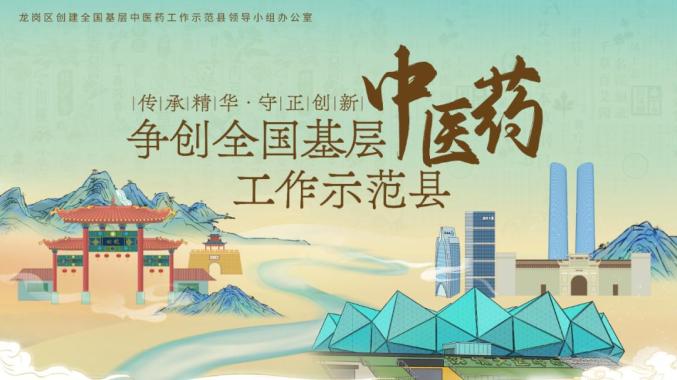
·
·()
《龙中对》上新!葛剑雄邀你探究“人往高处走”
马英九观看龙岗企业无人机表演!低空经济之路走出“龙岗样板”
深圳踏青地图,解锁春天的浪漫!
左右滑动查看更多>>>
·
··()美景
·
··
·
··(
·
··()美景
·
··
·
··(
·
·
·()美景
·
·
·
·
·
·(

继续滑动看下一个轻触阅读原文

深圳龙岗发布向上滑动看下一个
原标题:《临终关怀社工:用心陪患者走完生命的“最后一公里”|封面故事》